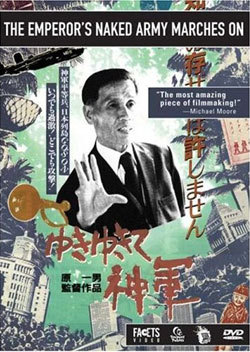
不平凡的人終造就不平凡事件,《怒祭戰友魂》其紀錄題材的奇特及爭議性,相當程度地預示這部紀錄片的絕對驚人。鏡頭下的現實生活宛如劇情片般充滿衝突、暴力、高潮迭起。除了因「一個難搞的激進人物」逐步挖掘出日本戰後軍隊因糧食缺乏而食人的駭人真相外,另外,整個紀錄過程中的法理與道德問題都讓《怒祭戰友魂》爭議性十足。
這個「吃人真相」留待社會、歷史研究去公審定奪。在此將偏重紀錄片的美學、道德、拍攝者/被攝者的互動關係。對於本片主角奧崎謙三所「扮演」一名追求真相的激進偵探角色,以及導演原一男在拍攝過程中的掙扎、道德與勇氣。此外,攝影機又是如何對真實人生產生更進一步、有意識與目的性的影響
《怒祭戰友魂》中,有著太多待解之謎與「不和諧」,為了釐清原一男與奧崎謙三對於這部紀錄片的想法,觀後特別找了《怒祭戰友魂》的製作筆記與採錄腳本藉此解謎,在影片與文字的對照下,卻發現更多驚人、更接近真實狀況,卻無法被拍攝的細節部分。不知能不能說是紀錄片的原罪,拍攝者捕捉到的真實,永遠是經由自身主觀所篩選的片段紀錄,當攝影機對準某一方時,景框外的真實卻也不斷地發生並成為過去,原一男序言便道:「沒有拍到的東西總比拍到膠片上的多許多」,這篇七十多頁的製作筆記,對於整部紀錄片的拍攝,留下極為豐富的創作歷程紀錄,以及更重要的-一個紀錄片導演的自省。
讓我們回到那些留在底片上曾經發生且幸運被紀錄下來的事實,「紀錄奧崎」的拍攝構想,原是另一名在當時頗具份量的日本導演-今村昌平所策劃,但由於種種原因,今村卻遲遲未拍攝,於是他將奧崎謙三介紹給原一男,當時的原一男已有《再見CP》、《戀歌1974》兩部作品,年輕甫嶄露頭角的原一男,其紀錄的對象都具有撼人的生命力量,原一男也以「Super Hero」來通稱他們。
然而,奧崎有的並不只是憾人的生命力量以矣,奧崎與原一男彼此間的不和諧,漸漸地開始從年齡、社會經驗、對於在影片中的「位置問題」蔓延開來,當奧崎知曉要拍攝他的並不是大導演今村昌平,而是年輕導演原一男時,他是失望的,在拍攝中後期,當原一男對他所提出的拍攝概念有所抗拒時,他甚至以此倚老賣老,冷嘲熱諷原一男「只是個年輕人,什麼都不懂」。
影片開始於奧崎的電器舖前,一台寫滿標題如「殺死田中角榮」、「反天皇」等抗議字眼的小貨車停在家門口。在一場朋友的婚禮中,奧崎以證婚人的身分,簡短、充滿自信地在婚禮上道出自己的經歷與國家觀。曾有殺人、傷害前科,十多年的牢獄生活結束後,開始從事社會秩序破壞等事件。在奧崎的一生中,有一個謎團一直未解:在戰爭結束後,為何兩名軍袍會被軍隊下令處死?為了解開這個謎,他與原一男的攝影小組,開始一一探訪戰後遺族,並進入新幾內亞,企圖搜尋當時日軍的犯罪證據。後來這些新幾內亞拍攝的底片被當地海關扣留,回到日本後,原一男對奧崎的反感達到極點,終於停止拍攝,直到奧崎攜槍誤殺了清水隊長兒子後,原一男才驚覺與奧崎那段「我想殺死清水隊長」的對話,並不是在開玩笑。在這段漫長的紀錄過程中(影片由八二年開拍,直到八七年才完成),原一男因有感自己太投入奧崎這個人的傳奇經歷,故影片剪接並非由他親自完成,而是找來鍋島淳來接替自己負責後期剪輯。
就《怒祭戰友魂》的敘事結構看來,原一男以「劇情片」的方式架構整部影片,如在拍攝前先進入現場(如拉麵店場景)作安排規劃,以及允許奧崎找替身充當遺族家屬等行為,當他與製片小林佐智子決定將重心放在奧崎謙三身上,而非戰後真相時,對於片中那些允許暴力發生的鏡頭,以及奧崎的刻意演出,原一男都忠實地紀錄下來,並將其視為「真實的展演」,原一男曾明言他追求的不是客觀的真實,作為被紀錄對象主體的「演出」對他更加重要:
我認為人即使在日常對話中,甚至在沒有人存在的情況下,表現演出的意識也十分強烈,對這種狀態我充滿真實的感覺。而我想將這回事置於鏡頭前,令它更加顯眼,也希望這種演出的意識可以更凝鍊。換句話說,是透過攝影機的存在,令這意識更加認真,倒轉來說,與其追求自然的自我,我更想捕捉認真演出時那種充滿生氣的時間,讓其燃燒。攝影機內電影膠片捲動的時間,是唯一貨真價實的時間。即使我的紀錄片被指責為充滿劇情片的製作方式,我也一概不予理會。
(稻田隆記:《訪問原一男導演》,《Flix》九四年十一月號,總五三期)
原一男對紀錄片的獨特見解,與謹守客觀第三者的紀錄片傳統截然不同,反而較接近一種「真實電影」(Cinéma vérité)的美學:拍攝者是自我聲明的參與者,對於煽動抱持著擁護的態度。然而這樣的紀錄態度,會不會使得攝影機成為一注催化劑,促使被攝者在行動上更加大膽狂妄?無論是奧崎與警方的對峙、叫囂及揮拳,還是假扮成家屬去探視那些隊長,假設原一男的攝影機不存在,奧崎恐怕以不會以誇張的攻擊姿態去拜訪,甚至質詢、逼供這些老軍官們。
奧崎並不安於扮演主角,更有意圖使自己成為這部紀錄片的導演,但這不代表原一男的主導權完全喪失。如在奧崎訪軍官妹尾幸男一段,因為對方的不肯坦白,奧崎大怒直接將對方壓倒在地上、猛揮拳,但隨即便被四個大漢制服,奧崎在地上掙扎、極為狼狽,然而原一男的攝影機卻繼續拍著,把奧崎一心想維護的英雄形象給徹底摧毀。他並沒有被強勢的奧崎牽著走,儘管奧崎拼命示意停止拍攝,但原一男反而將他最難堪的一面拍下來,無情地背叛了奧崎謙三的自戀要求;此外,原一男也在沒有告知奧崎的情況下,事先走訪拍攝場景、會見這些人物,預期哪些情況會發生,並在拍攝時等待這些預期效果發生。《怒祭戰友魂》簡直像是在「彼此信任」關係的缺席下,拍攝者與被攝者依憑奇特默契所完成的作品。
在誤殺事件發生後,原一男開始對紀錄片的拍攝產生迷惘,拍攝行為的道德底線究竟在哪裡?在他的製作筆記中提到,當初他拒絕奧崎,一方面是因為害怕,另外則是因徹底討厭奧崎;但倘若他是喜歡奧崎,甚至著了迷的把電影視為絕對事物,當電影的重要性已經超越所有的法律、倫理、道德,甚至比一個人的性命還要重要時,原一男究竟會不會選擇拍下這個犯罪事件?另外,觀眾究竟又是如何看待這部影片,是慶幸原一男的道德堅持,還是有些不懷好意地遺憾更驚人的場面沒能被拍攝下來?這是在紀錄片道德底線下的問題,以及在其神聖使命中的矛盾,而《怒祭戰友魂》則揭示了在紀錄片拍攝思維下引人深思,甚至是見不得人的陰暗面。
參考資料
原一男.極走攝製組編著,《怒祭戰友魂-製作筆記與採錄腳本》
四方田犬彥著,《創新激情:1980年代以後的日本電影》,北京,中國電影,2006
Richard M. Barsam著,王亞維譯,《紀錄與真實:世界非劇情片批評史》,台北,遠流,1996
湯禎兆著,《追求「演出」的紀錄片作家-原一男對現實的重構》,《電影欣賞Fa》,第七十九期,1996,頁26-28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